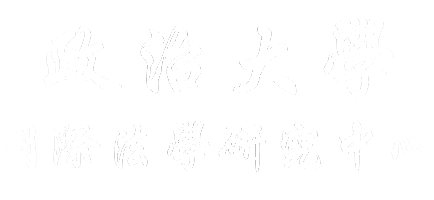The Center and Margin of JESSUP MOOT-一位老隊員的思考
傑賽普的中心與邊緣 [1]
The Center and Margin of JESSUP MOOT
──一位老隊員的思考

楊 肯
北京大學2015級法學碩士
*編注:原文為簡體中文。
一
今年是我在北大「傑賽普」模擬法庭比賽(一下簡稱「傑賽普」)代表隊中的第三年與最後一年。2015年時,北大隊終於從國內賽連續失利的陰影中走出、繼2012年以來再次奪得中國賽區冠軍,入圍4月份於美國華盛頓舉行的「傑賽普」國際賽。前一年中僅僅止步於國內賽的經歷進一步放大了我對國際賽的憧憬,畢竟,那裡才是整場賽事的「中央」以及它所有魅力的源泉。也正因為是首次赴華盛頓比賽,興奮與焦慮的裹挾模糊了那年國際賽的大多數記憶。好在,北大隊繼續在2016年國內賽中衛冕了冠軍。作為老隊員第二年再臨華盛頓,多少能較上次多些從容與冷靜;而想到自己即將離開這個令我流年三年的「小教派」(cult),便更希望能夠借此機會去觀察、理解這一有著「法科生的奧林匹克」稱號、世界上最大的國際性模擬法庭賽事,以及中國學生在其中的位置。
並非所有的模擬法庭隊伍會像傑賽普隊伍這般、在其成長過程中逐漸演化成宛如教派般封閉的小團體。參加「傑賽普」恐怕是最能夠讓中國學生領會為何霍姆斯(Oliver W. Holmes, Jr.)會將法律工作類比做是「戰鬥」的經歷。它的高門檻(如對較強的英語能力的要求)、長週期及強度,意味著希望取得勝利的隊伍需要將自身改裝一架堅實而高效的「戰鬥機器」;在我看來,正是在此過程中,中國的「傑賽普」隊伍也生發出了某種適應其本土需求的「想像」與「敘事」,以鞏固隊伍的意志力與行動力(抵禦比賽中不確定因素所引發的種種不幸)。 畢竟,他們已經為和「死線」(對於英文中「截止日期」[deadline]充滿自嘲的直譯)賽跑而熬過了太多個漫漫長夜、為了保持清醒而攝入了過多的咖啡因和垃圾食品,借遍了國外同學的數據庫賬號來補充法律研究,在不知不覺中與週末和假期成了路人──無論是在比賽的過程中,亦或是比賽結束後、需要將隊伍傳遞給後來者時,當初的參賽選手們需要一套故事來證明自己的一年中的付出是值得的。這套敘事所圍繞的核心便是所謂「普通法的技藝」:借助於準備比賽的契機,以大陸法為底色的中國學生便有機會去自我摸索普通法的技能與知識;在此意義上,每一個隊伍都有可能會是一座和隊員共同研習普通法的「學園」。而在當今中國法科生的心中,普通法技藝在智識上的價值與職業發展上的價值,都會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如此,向「新羅馬」進發的漫漫旅途便愈發像是一場關乎獲得承認、關於意義的「朝聖之旅」。大概是「朝聖」業已完成後所擁有超脫感,我倒是在的回望中愈發感受到中國學生自身對於「傑賽普」的認知是如何被這些想像所改變。一些模糊的想法,促使我試圖再回過頭來去追問,如此遙遠的、與中國法學教育並無多少直接關聯的「傑賽普」比賽究竟為何會吸引我們?我們又能從孜孜不倦的追索中得到什麼?
華盛頓燦爛的櫻花時節恐怕也是令選手們為國際賽前赴後繼的原因之一。
二
「傑賽普」肇始於兩位國際法教授的一次教學嘗試。1959年時,哈佛法學院兩位共同負責教授國際法課程的教授,Richard R. Baxter與Stephen M. Schwebel──兩人均曾在劍橋大學隨英國國際法大家勞特派特學習,先後被美國政府提名成為國際法院的法官──為學生們設計了一場名為「International Law Moot」的小型模擬法庭。[2] 參賽的兩只隊伍分別由來自美國的J.D.學生,以及來自加拿大與新西蘭的LL.M學生組成,分別代表一起由國際法院審理糾紛中的申請國與被申請國(Applicant and Respondent);比賽所設計的案例則緊貼當年的熱點事件、古巴革命政權針對美國人財產的歧視性徵收政策展開。學生在庭上的論辯表現讓兩位教授深感鼓舞,並決定以美國外交官、公法學者以及後來的國際法院法官Phillip C. Jessup來冠名這項賽事;哥倫比亞大學隨後加入了次年的第二屆賽事,「傑賽普」也由此迅速獲取了美國其他法學院的關注與青睞。時至1967年時,成為美國國際法協會執行主任的Schwebel已經需要操心將比賽交由各校輪流承辦所導致的資金不足及組織混亂問題。為此,Schwebel開始借用協會的資源來為比賽設置專門管理辦公室,尋求資金以支持非美國院校赴美參加比賽,資金來源既包括諸如麥克杜格爾等國際法學者的私人捐款,企業的資助,還包括美國國務院的撥款。[3] 陸續建立的制度保障成為了模擬法庭向全球推廣的堅固基石:1968年比賽首次向非美國隊伍開放,而到2016年時「傑賽普」已經能在全球範圍內吸引到700多所院校註冊參加、共130多支法學院隊伍赴美角逐國際賽。一個有趣的細節在於,我們可以美國政府撥款數據庫中得知,美國國務院國際毒品執法處(State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and Law Enforcement Affair)曾專門申請撥款以資助阿富汗傑賽普國內賽的舉行,並負責邀請教練來為阿富汗各大學隊伍提供模擬法庭訓練;在描述欄中,國務院強調撥款的最終目標在於提升阿富汗法律專業學生的教育機會、通過互動性的教學過程而練習批判性思維。
如果說國際公法系統因為其歐洲起源而不可避免地體現出「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c)的特徵,誕生於美國普通法教育的「傑賽普」模擬法庭賽事似乎也難逃「普通法中心主義」的宿命。普通法系法學院出身的同學在比賽中所取得的「霸權地位」從成績榜單上看來一目了然:在過去48年中躋身「傑賽普」國際賽決賽的隊伍中,僅有來自8支隊伍來自大陸法系背景國家(分別是埃塞俄比亞海爾·塞拉西一世大學[1972年亞軍/1974年亞軍]、比利時魯汶大學[1987年亞軍]、巴黎第一大學[1992年冠軍]、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1988年冠軍]、委內瑞拉安德烈斯·貝略天主教大學[1997年冠軍/2000年亞軍/2001年亞軍/2006年亞軍]、哥倫比亞安地斯大學[2009年冠軍]、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大學[2012年冠軍]和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2016年冠軍])。 [4]普通法系學生在比賽中所享有的「結構性優勢」,大體上可以被歸因於比賽自身的性質以及比賽的組織模式。一方面,比賽所試圖模擬的國際法院自二戰成立以來,便一直通過司法審判過程來澄清並發展相關的國際法規則與原則,並在此過程中生產了豐富的國際法院案例。由於國際法系統自身的種種特性,國際立法和國際法編纂的效果往往不盡如意,由國際法院所做出的司法先例(judicial precedent)反倒從此過程中脫穎而出,成為了國家與國際性法庭爭相援引的法律依據。 [5]歸根結底,這一切仍可以被追溯到美國與英國所共同締造並主導的戰後世界秩序,以及與之相對的、融入了英美傳統偏好的國際法體系。出於比賽競爭性與平衡性的考慮,「傑賽普」每年的賽題設計皆是圍繞最為前沿(因而往往也是法律上全無定論)的國際法問題展開。既成國際法規範的缺失,迫使選手策略性地訴諸案例、主張將法院此前已經確認的相關規範「情境化適用」(contextual application)於本次爭議中,或是請求法院根據己方舉證的相關國家實踐與法律確信(state practice and opinio juris),去確認某一新習慣國際法的存在,並依照該規範做出有利於己方訴求的判決。這一過程自然要求選手能夠熟練掌握所謂「普通法技藝」。另一方面,賽事活動無法脫離龐大且相對專業的法官的參與和支持,組委會於是便將眼光轉向了由過去的參賽隊員構成的「傑賽普賽友共同體」(Jessup Alumni Community)。恰好因為「傑賽普」門檻較高且又相對封閉、選手在其中投入巨大且又收獲頗豐,曾經在此舞台上叱吒風雲、如今已經在各個法律領域功成名就的選手們多少都會對此心存感念,甚至自掏腰包作為志願者重返這一舞台扮演法官的角色;有一位法官曾在賽後向我們開誠布公,說以法官身份回歸「傑賽普」畢竟可以「少些辛勞而多些樂子」(its more fun and less work on this side of the table)。不過,真正赴華盛頓出任國際賽法官的賽友們主要是普通法背景出身執業律師,因而也使得普通法學思維中的部分偏好被有意無意地延續甚至強化。不過恐怕正因如此,躋身國際賽、甚至是與強隊過招,才是中國隊員證明自己「未負初心」的理想方式。
三
北大法學院宋英老師的辦公室書架上至今仍然擺著一座已經略為褪色的小小金杯。儘管在現在的標準看來已經很是粗糙,這座不起眼的獎杯卻見證了大陸法科生向「傑賽普」舞台邁出的第一步,以及中國隊伍在其中所取得的最高名次。也正是在這間辦公室裡,宋英老師和我聊起了這次「遠征」中間的奮鬥與榮耀。這一切都起始於王鐵崖先生做出的一個相當臨時的決定,即北大學生有必要參加1989年的「傑賽普」國際賽。當年的隊伍僅含三名成員,分別是擔任領隊的李兆傑以及作為上場選手的研究生宋英和本科生凌兵。在準備比賽書面訴狀的過程中,兩位選手就索性窩在了燕南園中一間借來的屋子裡,沒日沒夜地查閱所能蒐集到的英文資料,再將稿子用打字機敲出來;領隊則需保證兩位選手的咖啡供給。仿佛是命運的安排,北大隊的兩名選手在淘汰賽階段首先就遭遇並擊敗了擁有二十人團隊的台灣大學隊,而台灣地區高校早於1977年起便成為這一賽事的常客了。北大隊隨後負於當年的亞軍,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隊:當時有一位據說是演員出身、氣質出眾的白人女孩穿著一襲紅色連衣裙上場,驚艷了滿是黑色西裝攢動的房間,最後又以其優雅而機敏的表現打動了全場法官,也令宋英老師感到心服口服。不過,北大隊已藉此一役躋身國際賽前八,這至今仍是大陸高校在「傑賽普」國際賽中所取得的最佳成績。[6]
當年困擾北大隊的各種外部因素如今多已不復存在。隨著邁向「國際化」逐漸被確立為是法學院的基本方針,「傑賽普」隊終於也能夠名正言順地向院內尋求制度上的支持。國際公法專業的易平老師於2009年回校任教後自願擔任了北大隊的帶隊教練,並在「北大傑賽普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而這個共同體如今正在逐漸轉型成為為每年新隊伍提供訓練支持強大後備力量。於2008年落成的法學院陳明樓在過去的幾年中成為了隊伍的固定據點──一樓裡的五個會議室十分適合隊員們集體閉關寫作或是討論,每年期末考試結束後,隊員們就會往會議室裡搬來抱枕和毯子、靠儲備在易老師辦公室中的咖啡、零食與外賣度日,只為專心趕稿。 然而也正是當隊伍無需再為上述硬件投入精力之後,隊員們才逐漸對一些散布在比賽各個環節中更為「隱性」的門檻開始有所自覺;對於我而言,思考的開端與基礎恰恰是北大隊在連續兩年「朝聖之旅」中的經歷與挫敗。
(攝於2016年(又一次)踩點交稿之後;滿桌的狼藉便是對一場惡戰的見證。)
「傑賽普」首先是一項國際性英文賽事,然而語言以及英語文化背景等因素在過去有關這一賽事的分析中卻似乎並未被給予足夠的關注。各隊需要在賽前以英文撰寫案件訴狀(memorandum),賽中上場以英文進行口頭答辯(oral presentation);從準備到上場,整個過程都貫穿著高強度的英語能力運用,特別是檢驗非英語母語的學生能否運用英文進行記憶、思考並完成最後的表達。北大隊一直在國內賽中以口頭辯論見長,多少說明了隊伍英語能力在國內隊伍進行橫向比較時仍占有不少優勢。英語能力也是隊伍在每年招新時所重點考慮的素質之一,儘管這一要求也實質性地影響了隊內的性別構成。 [7]我在2014年剛剛加入隊伍時,當年全隊的托福平均成績已經接近114分(考試滿分120分,全隊峰值為118分;我本人則是在隊裡摸爬滾打了一年之後,才終於考出了上一年度的「平均水平」)。然而能夠攢出前述的「高配隊伍」仍然屬於少數情況,英語能力在多數情況下仍可能成為影響北大隊備戰及上場比賽過程中的短板因素。美國法學院中高強度的閱讀與寫作訓練使得美國隊伍可以等至11月份組隊,並於法學院學期結束後(通常是聖誕節後)開始集訓,全隊用將近20天的時間完成訴狀的寫作(「傑賽普」每年所設置的訴狀提交截止時間集中在一月中旬,這一時間點大體與美國法學院寒假結束時間相重合;對於中國選手而言,這又往往是學期末最為水深火熱的時間)。北大隊這些年來均是在每年國際賽後即開始著手物色下一年的隊員,在6月前完成面試與組隊,以便在暑期布置培訓以及對明年賽題所涉國際法領域的事先「預習」,等待組委會於9月份正式公布賽題。比賽規則為訴狀設有字數限制,一份優質訴狀的字數通常會在9000詞上下;訴狀中的注釋數量則會決定法官對該訴狀法律研究深度的第一印象。2012至2015年評選出最佳訴狀的平均注釋數為218個;引注數最多的隊伍為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通過引入大量美國法判例作為國家實踐的例證,使得總注釋數達到了295個。[8] 這多少也意味著參賽選手在準備過程中必須蒐集、閱讀大量的材料,並以此為素材來組織體系化的法律論證。在我個人的經歷中,直接接觸並嘗試閱讀大體量的英文材料往往使人失去頭緒、研究事倍功半,將信息提煉並重新表達的過程也絕非容易。恐怕正因如此,北大隊即便會預先「備戰備荒」並延長寫作周期,英語能力上的「力不從心」仍然無法解決時間上的壓力。
除了訴狀寫作之外,隊員們發現自己同樣有必要把精力投入至口頭答辯環節的「微調」上,即注意自己的表達風格(advocacy style)能夠在細節上契合外國法官的語言習慣。比賽的口頭答辯環節由雙方各兩名隊員上場表達本國之立場及法律依據,法官則會隨時打斷發言並就其感興趣的法律爭議問題進行提問;考慮到律師的職責即在於「幫助法庭」發現法律──這多少也是一種頗為「普通法」的理解與自我定位──律師能否直接回答法官感興趣的問題並同法官間保持流暢的溝通,便成為了法官賽後評分的重要依據;用一位法官賽後的評論來形容,選手僅僅將具有說服力的論證內容了熟於心是不夠的,他(她)所選擇的表達還應讓法官足夠「受用」(「massage your judges with words」)。然而,哪怕北大隊員早已不再被發言流暢度或眼神交流等問題困擾,如今卻也無法就溝通中的細節問題有十足的把握。除了所有上場隊員都需應對的、由法官個人偏好所帶來的種種不確定性,中國選手還需要對自己的語言習慣保持關注,以避免在印象上失分。來自美國、如今在法學院訪問交流並擔任北大隊教練的喬一夫(Prof. Joseph Pratt)老師,時常會在訓練中提醒我們與表述相關的細節問題。例如,法官提問後,隊員為了表示自己接下來的論述將會是針對此前問題的直接回應,往往習慣性地在給出實質回答前先在開頭加上一句「We understand your concern, your excellence」(「法官大人,我們理解您在這一問題上的考慮」);儘管這一短句僅僅是用於提示並表示轉折,喬老師卻總會指出「your concern」的用法多少讓他這樣的英語母語者聽著別扭──在他的語感與習慣中,「concern」更多是指代親密關係語境下(如父母與子女間)的「關懷」或「擔憂」。因此當我們在「法庭上」頻繁使用這樣一個「非法律」的詞語時,多少會令他感到「出戲」。相類似的,中國選手在母語環境下的表達習慣同樣也可能影響其在場上的風格。一位迎娶了日本妻子的法官就曾表示對中國學生回答問題不夠直接表示理解,因為他十分明白「從亞洲人口中『擠出』一句直截了當的回答會有多麼困難(I know how hard it could be to squeeze out a direct answer from an Asian people)」。一位法官曾在賽後點評北大選手的表現時,特別強調選手應當使用法言法語來直接回應法官的問題,少用一些並無實質內容的「外交口吻」(diplomatic tone),而這極有可能只是因為選手在不經意間按照漢語思維來回復法官而已。不過,為語言或表達風格所困擾的絕非僅有中國隊伍:2015年國際賽時北大隊曾於初賽階段遭遇哥倫比亞安地斯大學隊(該隊曾於2009年問鼎冠軍)並被後者完勝;震驚我的不僅是該隊扎實的法律研究,更是他們充滿激情而又靈活生動的風格。出乎意料的是,這支隊伍在淘汰賽32進16的階段即輸給了渥太華大學。在賽後的晚宴上,哥倫比亞隊的一位小哥略帶無奈地將失敗歸因於「場風」問題──「(沒辦法)我們拉美人,就是這般熱情洋溢……」(「We Latinos, are just passionate……」)。這一故事恐怕是英語國家隊伍在「傑賽普」國際賽中占據支配地位的一個小小的注腳:儘管每年闖入國際賽淘汰賽的非英語國家隊伍可以占到這32強中的半數以上,但這些隊伍多半會在1/4決賽時淘汰殆盡。在過去十年的國際賽中,非英語國家隊伍只闖入1/4決賽9次;而在2007、2008和2014三年中,1/4強則全部由英語國家所包攬。 [9]
令隊員們感到焦慮的是,儘管這些語言或風格上的瑕疵可以通過「技巧性處理」(例如調整口頭習慣、回答時直接以「Your Excellence[法官閣下],……」開頭,而避免使用「可能」[10] 令英語母語者感到詭異的「We understand your concern」)而得以彌補,這也僅僅是一種「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辦法(an ad hoc solution)。對於北大隊而言,降低因語言或者風格失分這一隱性風險的最優解便是通過頻繁的模擬訓練來進行「試錯」。十分有趣的是,可能是得益於大量的賽前訓練,國際賽中倒可能出現北大隊選手在熟練度和流暢度上優於英語母語國家選手的情形。
四
同2015年的經歷相似,北大隊在今年的淘汰賽上再次因為毫釐之差而未能進階全球16強。不過,至少我們還能夠在最後的晚宴上聽到主辦方大聲念出北京大學的名字、並帶著驕傲上台從主辦方手中接過一份紅木獎牌。然而剛好就在領獎完後的離場過程中,我在舞會大廳後門處看到了兩個亞洲女孩──此時頒獎儀式尚未進行到前四強,大廳前方的氣氛正在愈發熱烈;而就在同一大廳後方暗處,這兩位身著華美晚禮服的女孩選擇趴在餐桌上、將頭埋進胳膊裡,百無聊賴地玩著手機;無獨有偶,就在桌子的對面,恰好又坐著一位同樣是在玩手機的非洲男孩。挎著相機的我鬼使神差地溜到了她們的背後,記錄了他們「置身其中、卻又游離其外」的瞬間。照片前景中留守在陰影中的女孩們與遠處燈光下歡呼的人群間的巨大反差令我深感震撼。這種感受多少因為這一小小的景觀似乎再次印證了我對「傑賽普」賽事裡存在的「中心-邊緣」的模糊認識;它似乎再次提示我,從邊緣出發前往華盛頓的朝聖之旅是多麼漫長與困難,許多隊伍中途折返,有些隊伍則空手而歸;倘若不是手中獎牌的的重量,我們又何嘗不會墜入到相同的心境中呢? [11]
(在我的相冊中,我將這張照片命名為《邊緣處》)
早在「傑賽普」問世之前,哈佛與哥大法學院內早已打造出本院內的模擬法庭品牌,如前者的Ames Competition(1911年)與後者的Harlan Fiske Stone Moot Court(1925年)。[12] 此類模法賽事早已發展成為各院的年度性活動,聯邦最高法院與巡回法院法官前來為決賽捧場支持也已成為慣例;此類模擬法庭也由此成為院內最優秀的同學首要瞄準的競技場──這場賽事許諾給他們的榮譽,注定會成為打開他們未來法律職業生涯通往上升捷徑的金色鑰匙。儘管「傑賽普」仍然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模擬法庭賽事,其在美國法科生中所享有的威望(prestige)卻未必有我們想像得那麼高;[13] 一位康乃爾法學院的傑賽普隊員就曾向我坦白,若不是自己最優秀的同學選擇參加院內的模擬法庭,自己恐怕並沒有多少機會擠進「傑賽普」隊伍。而對於中國學生而言,國內的模擬法庭教育與賽事仍在起步之中;在此大背景之下,「傑賽普」比賽的規模與國際化模式,其所宣揚的國際主義精神,[14] 以及這一比賽所許諾的「普通法(自我)訓練」,便能顯得格外吸引人;如果說美國法學院學生可以將「傑賽普」視作是可供自己挑選並一展身手的訓練場,中國學生則會傾向於將同一比賽想像成是普通法的「學園」──倘若自己的隊伍具有足夠的意志力去走完這一學習過程、掌握相應的知識與技能,便有可能藉此實現向「中心」的流動,在國際賽中放手一搏。
倘若說何美歡老師在其《論當代中國的普通法教育》中的判斷無誤,即,主動走向「美國化」是中國法學教育的唯一出, [15]那麼中國學生對「傑賽普」所顯示出的熱情似乎正是對此趨勢的呼應;也正因如此,有關「中心-邊緣」的認知與話語才不會在中國的「傑賽普」共同體中流行,因為對此結構的認知除了令人沮喪之外,並不會為學生們克服這條不得不克服的征途以任何幫助¬──或者說,唯有中國學生咬牙挺過當前的窘境,方能看到一點點變革現狀的可能性。然而,如果說何老師曾以一己之力在清華法學院內部撐起了「第二個法學院」、以便為使中國學生能夠同時接受優質的普通法訓練,[16] 我們不應想當然地把同樣高的期望代入至「傑賽普」比賽中。恐怕正如何老師所指明的那樣,「比賽」的性質使得老師只能以非常有限的方式介入學生們的訓練;隊員只能以「自我學習」或「共同學習」的方式來接觸判例、成文法規、評議。[17] 在「傑賽普」中,任務的壓力則迫使此前僅僅習慣成文法訓練的同學以最為快捷的方式學習某一特定領域的國際法律規範,並根據訴訟雙方的特定立場來積累材料、建立論證;這樣的準備模式往往是以犧牲對於國際法的體系化認識為代價,而比賽的創設者恰恰期望賽事的推廣能夠刺激全球法科生對於國際法的關切、信念與想像力。至此,國際公法的知識僅僅淪為比賽所需要的、缺乏生機的「素材」。
本文絕非意圖用「反智主義」的責難或是「中心-邊緣」來給中國學生踏上朝聖之旅的熱情潑下冷水;「中心-邊緣」結構的描述更多是為了說明中國隊伍所需面臨的額外負擔,以及他們在消化這些不利因素時所可能付出的代價。北大隊的不少傑賽普賽友因為這段經歷而走上了赴美求學的道路,一心希望接受純正美式普通法訓練的試煉,而隨著這一共同體的壯大,還會有更多的北大校友走上這一道路。我很期待,當這些校友們回國之際,也會帶著他們當初從「傑賽普」中所收獲的種子,並將他們耐心栽下。等到木已成林時,那些再次決定走上朝聖之旅的師弟師妹,也許能少些焦慮、多些從容。
[1] 筆者在此感謝易平老師對本文的修訂與建議。
[2] Stephen Schwebel, Remarks by Stephen M. Schwebel,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3 (March 25-28, 2009), pp. 407-408
[3] Stephen Schwebel, Remarks by Stephen M. Schwebel,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03 (March 25-28, 2009), pp. 407-408
[4]每年比賽的情況皆已由組委會公布於其網上數據庫,具體請見:https://www.ilsa.org/jessuphome/2014-08-15-09-28-47/jessup-archives。
[5] Hersch Lauterpach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22.
[6]共有來自26個國家的39個隊伍參加了1989年的「傑賽普」國際賽。
[7]十分有趣的是,由於美國法學教育中往往在觀念上默認男生應當擁有更強的表達欲及相應能力,因而也往往使得男生占到了選手中的多數。
[8]傑賽普組委會每年會評選最佳申請國訴狀與最佳被申請國訴狀獎,各隊訴狀也被上傳至傑賽普檔案庫以供之後的學生下載。具體請見:https://www.ilsa.org/jessuphome/2014-08-15-09-28-47/jessup-archives。
[9]需要說明的是,此處所謂「英語國家」包括所謂的「英語文化圈」國家(Anglosphere,即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五國)
[10]我曾在賽後的交流環節中專門就“we understand your concern”是否符合美國法庭用語的問題向美國法學院的幾位教授請教,其中就有回答表示這一表述並未讓他們覺得存在問題;故出於嚴謹考慮,此處插入“可能”的限定。
[11]亞洲隊伍在「傑賽普」國際賽的社交環節中往往難以玩得痛快,導致這一結果的可能有多方面的因素:組委會的不少活動設計多少是從大多數歐美同學的偏好出發;大部分活動都會安排DJ來播放聲音巨大的流行音樂,而更加偏好彼此聊天的亞洲同學便只能躲到相對不那麼吵鬧的角落裡,彼此在對方耳邊把想說的話吼給對方;還有另外一些更為隱性的因素值得我們關注,如,美國法學院模式下的高門檻使得法科生們多少會自帶一種「天生傲驕」的心態;為此他們最多也就和商學院的兄弟們玩到一起去,本科生則壓根不屬於他們的世界。無獨有偶,來自亞洲的選手基本上是以本科生為主,且又往往顯得稚嫩。大概是因為上述原因,這兩年的傑賽普國際賽中北大隊更多是和來自中國的其他隊伍,以及日本隊和馬來西亞隊等亞洲隊伍泡在一起(二國的隊伍也同樣是由本科生構成)。
[12] Harlan Fiske Stone Moot Court系以哥大法學院校友、院長以及後來最高法院大法官哈蘭·斯通的名義所設置;非常遺憾的是,除設立時間外,我未能查到更多有關Ames Competition的歷史資料。
[13]有趣的是,來自挪威的訪問教授Morten Bergsmo認為以模擬法庭、辯論的方式來訓練法學學生仍然是相當「英美」的做法。作為一名曾經的參賽選手,Bergsmo教授認為挪威、德國最為優秀的法科生恐怕並不會對此賽事非常積極。
[14]今年國際賽決賽環節中一位發言者的勸勉令我印象深刻:「只要你能保持你在這裡所顯示出的活力與風險精神,你便完全沒理由擔心國際法僅是某種理想主義。」(“so long as our students maintain the energy the excitement and commitment you saw here, you would have no reason to fear, that international law is some kind of idealism.”)這大體可謂是“傑賽普”的官方意識形態──它恰恰是基於「哥倫比亞學派」、傑賽普本人門徒們所嘗試描繪的圖景:來自世界各國各民族、卻又共同分享著同一套國際法話語體系的國際法律人,將會攜手形成一個「無形的學院」(invisible college)並成為人類福祉的守望者。關於“哥倫比亞學派”的出處,請Samuel Moyn, 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93. 不過,這種國際主義情懷對於大多數中國選手而言,似乎仍然顯得是過於縹緲和抽像了。
[15]具體內容請參見何美歡老師《論當代中國的普通法教育》第一章,〈全球化:在中國法學院教授普通法的一個理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
[16]趙曉力:《一個人的法學院──紀念何美歡老師》,見愛思想網: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751.html。
[17]何美歡:《理想的專業法學教育》,載《清華法學》,2006年第3期,第128-1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