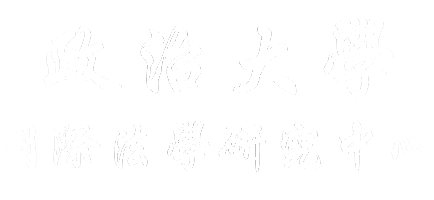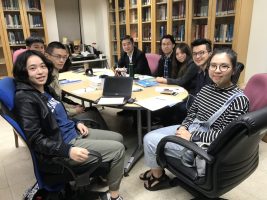傑賽普:診斷式解析
宋承恩
學、經歷:英國牛津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傑賽普裁判
網路世代新人類,在忙碌接收圖像之餘,如果有時間給文字,也喜歡單刀直入,立即得到實用的教戰資訊,最好集成懶人包,再配上圖解,即使不能連貫,沒有邏輯,也沒關係。
傑賽普可以秒懂就好了(可惜!)。不要絕望,廣大的閱聽人(在哪?),你們的呼聲我聽到了(I hear you),就讓我試著對症下藥,以診斷式入手(clinical approach),解析傑賽普這個看起來非常炫的東東。
傑賽普不是辯論比賽,是模擬法庭
傑賽普不是話說得漂亮就贏。但話說得合宜,會幫助別人聽進你的論點。
「辯論比賽」沒有抓到傑賽普的核心。打傑賽普,口說是重要的,但口說是為了呈現論點,特別是以簡潔、精確、有效率的語言,呈現論點。「模擬法庭」與辯論比賽的差別,是法庭必須「依據法律,作成權威性判斷」。模擬法庭雖然不需要作成判斷,但論點必須於法有據。
至此,我們具體而微的點出了傑賽普如何論輸贏:
- 隊伍論據的呈現,是否「像個法律人」(lawyerly);
- 論據的呈現,包括書寫與口說;
- 如何「像個法律人」,至少包括對事實與法律的理解與解釋、適用法律、分析與歸納、推理與論辯(參作者前文「傑賽普困思」at https://goo.gl/CnhraF);
- 但傑賽普的輸贏不是看案件或論點的實體勝負。這點是重要的,因為傑賽普問題的設計,埋藏了先天的平衡:在某些問題點上,聲請方(A)的法律立場是弱的,但在其他點上,出題者會將情勢倒置,使法律立場不利於應訴方(R)。此時,要看的就不只是就爭點而論,法律立場究竟為何,而是更深的,看居於劣勢的一方,能夠產出如何挽回不利的論點。
由上,不難理解傑賽普裁判的評分單中,為何要求裁判就隊伍對事實的理解、對法律的知識、研究是否透澈、呈現的方式是否有架構與條理、書狀的引註、文法與風格、口說的語言使用、氣勢、以及時間掌控,逐項評分。
簡單講,傑賽普所看的,是在上述意義下,那一隊能作出較優的論據(arguments)。
試舉2018年的一個問題為例:A與R在進入國際法院前,即因沒入水下無人航行器事件,涉入仲裁。但A自始即主張仲裁庭無管轄權,拒絕參與仲裁,並續在國際法院前,主張仲裁判斷無效。同時,題目設計上表明,仲裁庭已作成判斷,認為自己有管轄權。問題來了:A在國際法院前欲主張仲裁判斷無效,是否繼續以仲裁庭無管轄權為理由?
國際法上,有所謂的法庭/仲裁庭得自行判斷自身是否具有管轄權原則(competence de la competence),使仲裁庭一旦組成,有權處理有關自身管轄權的爭議。在此原則下,A的立場是非常不利的:如何在仲裁庭已作成具有管轄權的情況下,繼續爭執此點?此時A重複向來認為仲裁庭無管轄權的論點,是不夠的,而必須直球對決competence de la competence原則:處理為什麼國際法院得以審查仲裁庭就自己管轄權的判斷,以及如何。若是A就此攻城略地,R可能就必須同樣選擇直球對決:此時只重複competence de la competence,是不夠的。
也就是說,題目故意設計為優劣不平衡局勢時,往往是進深挖掘論點的邀請。此時停留在表面原則,只會陷於各說各話。這正是傑賽普有趣的地方:題目不但映照現實(例如在南海仲裁中爭執管轄權的一方),還要參賽者進入真實世界無法處理的問題(例如該方選擇在庭外放話而非入庭陳述法律見解)。面對這種既擬真又真實無解的題目,決勝點在對議題的理解與論據的提出。論點必須打廣且深,而且帶有創意。若是沒有看到這樣的層次,是我們對傑賽普的理解還不到位。很可惜,這是台灣各隊今年普遍的情況。
國際法是什麼?能吃嗎?
這個世界充滿著對國際法的誤解:你可以輕易的在電視報章上看到名牌教授大談政治決定一切,在自己立場受不利對待時,卻又高談「法治」。傑賽普不給你猶疑的機會:它的情境是國際法院,擺明了是法庭前的法。
什麼?國際上還講法?還有法庭?
有的,雖然它不完美。但它的缺陷,正是國際法迷人的地方。
國際法庭法第一個不完美,是國與國的爭端不容易告得成,因為國際法院的管轄權,立基在「國家同意」原則。在國家不同意被告時,你告不了他。因此,在傑賽普的情境,歷來的案子都設計成 A、R兩方經達成特別合意,賦予國際法院管轄權。
2018年的傑賽普,打破了此一慣例,是第一個依兩方所締結條約中的爭端解決條款,提至國際法院的命題。也就是說,過往隊伍在傑賽普中,基本上不必處理的管轄權問題,在2018年的命題中,成為四大爭點上個別可得爭執的問題。
這點是2018年隊伍的一大負擔,同時也是裁判的一大挑戰。在台灣尤其如此:我們的法學教育,極端不重視國際法(奇怪吧,對這麼需要國際法的國家),看到同學願意花時間讀書思考國際法問題,老師們老早感激涕零,「何忍」叫同學再去了解極端複雜的國際法院管轄權爭議案件?台灣目前還上不了國際法庭,讀這些何用?
如同預期,我看到的2018年台灣比賽,沒有隊伍處理了可能的管轄權爭議。但這並不表示它不存在,我們可以拭目以待國際賽的情形。
國際法庭法第二個不完美,是國際法的法源。常聽到人信手拈來聯合國大會決議、國際會議宣言、國際專家團體原則,但這些是「法」嗎?可以作為法院判案的依據嗎?這些,使我們必須處理國際法法源的問題,包括什麼是條約、什麼是習慣國際法、什麼是「軟法」。正因成法的困難,國際法大概是唯一區分現存法(lex lata)與未來想望法(lex ferenda)的法領域。更深的問題還有,未生效的條約是否可能包含具拘束力的規則,國際習慣法能否拘束異議國家等。國際法的規範性,不但困擾著作國際法的人,還構成法理學的課題。
難怪在早先時代的台灣賽事中,老師們必定問「國際法的法源是什麼」。但是老師,傑賽普要的不是教科書上的答案,而是應用在個案,與論據相關的答案。
傑賽普迷人之處,在參賽者必須直接面對國際法的不完美,同時扮演國際大律師,為論點辯護。
裁判的兩難
傑賽普是一方的陳述表演?兩方的唇槍舌劍?還是三方的比武大會?裁判,究竟是不是傑賽普的「一方」?如果不是,裁判為何要問問題?在傑賽普比賽中,裁判表面上扮演法官,實際上角色為何?
從裁判的角度,其實面臨兩難:全然尊重辯士,不加打擾,每位在台上都舌燦蓮花。法律之論辯之學,是否對問題充份了解,唯有經過詰問與「友善的交換意見」,才能知道。同時,裁判必須提問,也表示裁判也必須準備案子;與辯士有所互動,也能顯示裁判聽懂辯士所講的。
但若是裁判介入過深,甚至與辯士就單一議題纏鬥不休,豈不變成裁判與辯士間的辯論大賽?過去在決賽階段,曾經出現五位裁判輪番提問,炮火猛烈,形成「裁判提問大賽」的情形。裁判提問過於積極,還有破壞辯士口語呈現結構,甚至導致討論碎片化,個別議題化的效果。有些論點,是必須仔細推敲,慎密分析,始能理解或導出結論的。問題是,辯士在台上,有沒有如此空間?還是,不待析述,就被跳入的裁判打斷?
為避免此種情況,傑賽普給口說裁判的指示,是盡量尊重辯士的呈現結構,提問的時間以不超過辯士所有時間的百分之25為原則。雖然該指示也完全尊重裁判,如果認為有測試的價值,甚至可以由開頭的時間分配開始問起。(https://www.ilsa.org/jessup/jessup18/Administrator/2018oraljudgingguide.pdf )
問題的類型
多年來,我在傑賽普所聽到的裁判提問,可以分成以下幾類問題:
第一類是「基礎知識性」的問題,例如問到某個機制的基本面向,某多邊條約的締約情況,或某個概念的意涵。有些老師會提一些常識性的問題,例如目前聯合國的會員國數目,某個條約的訂定年代。有些老師會問某個案子的具體事實與判決重點。這些問題的導向是一致的,是測試參賽者是否真正理解所引論據,即基本功是否紮實。
第二類是「要求澄清性」的問題。經常見到的情形是,參賽者會講論一大堆,卻沒有適度的提綱挈領,把最主要的論點,用一句話講出來。或者,參賽者對於困難問題,隱藏在模糊語言背後,不願將真實立場清晰表述出來。此時,裁判會「尋求真意」,要求辯士確認其立場,或測試其有沒有能力用精簡的用詞與語言,作法律陳述。
第三類是「引申性問題」。有些主張,推到一定程度,似乎可以接受,但若推到極致,往往產生不合理的結果。有些原則,在某些事項上聽來有理,但適用到其他可資比較的事項,可能就不一定如此。或者,在陳述中,會察覺說理是基於特定的邏輯或哲學立場,例如2018年有好幾隊以「兩造沒有就仲裁程序訂定細則」為由,主張仲裁過程中出現的種種行為不能認為違法(嗯,好熟悉的說詞)。此時裁判可能問,陳述者的法哲學立場,是否認為「凡未被明文禁止者,皆為許可」。此類「引申性問題」,顯示裁判與辯士一同推理,進而探究某一說法,推到極致,或比較而言,或推至更抽象的上層,是否出現原本考慮未及的問題。這類提問是與論據互動較深的(engaging),說不定可以映照出原本的思考盲點。畢竟,法律的訓練,是要人想得週全,面面俱到。
第四類是「政策性問題」,是在實證法之解釋與適用,或「就法論法」以外的問題。有些牽涉法律如此規定,背後的理由與所追求的目標;有些牽涉法律如此適用,是否能導致公平合理的結果;有些甚至牽涉法律制度為什麼應該/不應該如此規定。國際法上充滿了這樣的問題。思考法律背後所追求的實質目標,原本即應該是法學教育的重要一環。法律研究對象是規範,原本即為社會所存在。法律制度的良窳,與不斷檢討,是法律演進與改革的動力。可惜的是,台灣的法學教育、國家考試、乃至司法官訓練,對「正確」適用法律的重視,似乎遠超過跳脫框架批判性的思考,以致台灣的法律人普遍不擅長、不欣賞,甚至不敢思考法律背後「為什麼」的問題。這可能是台灣的代表隊,在國際賽尚待亮眼表現的一大原因。
回答問題的「要」與「不」
既然在傑賽普,與裁判應答是如此重要,如何回答好裁判的問題?謹提出以下的「雷區」,以及穿越雷區的方法。
不要把裁判當老師,裁判只是與你討論法律問題
也許是從小教育的影響,台灣的同學習慣性把「老師」當成權威。這與西方博雅學堂上,權威就是要被挑戰的想法,原本已有極大差距,在必須採取立場,並據以攻防的傑賽普,更是如此。
在台灣的傑賽普中,由於「把裁判當老師」的心態,造成許多奇怪現象。例如,一遇到裁判提問,就翻檔案到事前準備好的那一頁,朗誦行禮如儀,彷彿裁判要的只是教科書上的答案,但對更進一步的問題,卻無力回答。久而久之,原本應該與裁判之間有所對話,卻越來越像台上台下的口試。又如,裁判一提出問題,隊友或研究隊員立刻振筆記下,好像裁判在上課,老師在給答案。我就曾聽到我的詰問內容,在日後的場次被「採用」,作為攻擊對方的論據。事實上,我作為裁判所提出的,只是個挑起話題式(provocative)的問題,並不表示裡頭的見解是對的,或是毫無爭議的。
這些都是把裁判當老師,把老師當權威的遺毒。有時,裁判只是提出反面論據,或指出有所爭議之處,想知道你怎麼看。這時候裁判只是想跟你討論法律問題,並沒有說你錯他對的意思。不妨正面接受有爭議,但不卑不亢陳述自己的見解,甚至指出裁判所說可資再考慮之處。
要讀心,真正聽懂問題
「聽懂問題」至少有兩層意思:第一是理解問題在問什麼;第二是理解問題的方向(what the question is leading to)。
前者很大部分是英文的問題:有些隊伍不習慣裁判的用字、腔調、或說話方式,而遭遇暗流。在台灣比賽,問題相對單純,大家還能用著台灣人特有的英語,溝通愉快。國際賽的參賽者,就必須面對各種英文的腔調。作為一名口譯,我理解其中的困難。破解之道唯有苦練。我曾經為了口譯重要講者,反覆聽其腔調十多天,始稍能應付。除此以外,法律的論述,要聽懂是困難的,特別是裁判在概念推衍的過程,或為了特定或精確化,使用較長的句子,挑戰特別大。近年來,我發現同學們越來越無法聽懂長句子,表示平常並不習慣以口語英文作法律推演。這是個危機,但這還是法律英文的問題。
長句子困難,短句子可能更困難,因為不容易立即理解裁判真正在問什麼,或者,在簡短問題背後,還隱藏著怎樣的問題。台灣同學另一個常見的問題,是只聽到問題的表面,卻沒讀懂提問人的心(mind)。法律英文是精細的語言,一個用語,一種表述方式,一個破題角度,都有它的意義。法律人聽人說話,不但要聽「話」,更要「讀心」。不但在傑賽普,未來在做律師、談判,甚至協調或決策,都需要這樣的能力。
要認真聽對方所說的,但要在自己的架構下回應
傑賽普建立在「兩造對立」(adversarial)的架構下。在比賽的設計上,第一階段兩造辯士的陳述,視議題性質,有攻有守,重點是讓兩造的論點能夠呈現。第二階段中,先由聲請方針對應訴方陳述做反論(rebuttal),再由應訴方針對聲請方的反論作再反論(sur-rebuttal)。
作為裁判,我的目標是讓各個陳述者,有公平的機會將論點陳述出來,並且與對方有所交鋒。辯士在說話時,我一定將所講的要點,逐點紀錄下來,並要求對方作回應。也就是說,應訴方在陳述時,必須針對聲請方的論點,提出回應或反駁;聲請方反論時,必須處理應訴方所陳述的論點;再反論則只限於處理反論所提出的論點。在設計上,傑賽普植入針鋒相對,讓真正好的論據能脫穎而出。裁判必須讓此一設計,能發揮其功能。
茲以2018年傑賽普出現的兩個情況,進一步說明。情況一,A方提出了一個細緻縝密的論點,並不容易立即理解,但得以完整陳述。未料,R方的辯士一上來,並沒有要加以回應的意思,只想照原本的架構陳述。經裁判指出,A方的論點值得認真回應,R方辯士仍一頭霧水,迫使裁判必須為其摘述該論點。這顯示 A方陳述時,R方並沒有認真對待,或者沒有聽懂。這是不夠理解傑賽普兩造對立的結構。
情況二相反,是「非常」注意兩造對立:R方一上來,首先針對A方論點,逐點指出不符事實或值得反駁之處,足足花了五分鐘才進入自己的架構。此為反例:較佳的作法,應是依循自己的架構陳述,到了相關處,狠狠的反駁對方,而不是讓反駁凌駕於陳述的順序與結構。
台灣傑賽普的危機
希望以上的「教戰診斷」,有助於非常務實的了解傑賽普此一活動的特性。最後,容我對傑賽普整體,作簡短的診斷。
台灣傑賽普三十多年,在整體對英文口說不友善、國家不重視國際法、法學教育不利批判式思辯的艱困環境,一路走來,靠的是參與者的熱情與投入。沒有特質報酬,失敗而歸的多,勝出出國比賽的少,不為別的,只為參與者個人在過程中的收穫。曾經在一次推廣講座中,一位老師坦率的問,這樣需要投入這麼多時間的比賽,沒有學分,沒有獎勵,學生有什麼誘因參加?有什麼用?在座的另一位,代我回答:「無用之用,是為大用。」
但傑賽普的危機,不只於缺乏資源。對我而言,當前台灣傑賽普最大的危機,是失去台北以外學校的參與,正逐漸變成台北的各大學在玩的遊戲。失去參與者的傑賽普,就不能算是傑賽普。這背後當然有向來的結構性問題,但這對台灣整體,是不好的,也是不應該發生,或任由其惡化的。主辦單位如果還有一點資源,應該正視這個問題,採取積極的措施,扭轉一下台灣的國際法教育,或藉由推廣傑賽普,反向提昇學校及同學對國際法的興趣。